七斤是我一个堂哥的乳名。他生下来以后,接生婆用老秤一称,足足七斤,他母亲便在产床上给起了这个名字。
我和七斤哥从小一起长大,后来又一块儿上学,直到中学毕业。我们常常形影不离,为了一道练习题,我们讨论成了红脸“关公”;假期里,我们相约上山挖草药,准备新学年的学费……一切往事恰似记忆中明亮的灯,永不熄灭。
十五岁那年,七斤哥便失去了父亲;十六岁时有了继父,而父爱却只在梦里才有。他一度陷入痛苦与孤独之中。那时,作为堂弟与朋友的我,却没能给他安慰与关心。加上有些人的捉弄、奚落,继父对他的折磨,村里人冷冰冰的目光……七斤哥失学了。我没有了同路人,心里满是失落与愧疚。
从此,七斤哥走向了贫瘠的土地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成为一个十七岁的地道农民。后来,我考上了大学。假期回家后,我不敢站在七斤哥的面前,告诉他外面世界的精彩,不忍问询他的生活境况,我怕想起《故乡》中的闰土;我只有远远的望着他,望着他那在烈日下弯腰劳作的背。那微驼的背,像一个沉重的“?”号,在向土地与生活叩问;又像一张满弓,弦上搭着汗水与泪水铸成的人生之箭,正射向土地与命运的心脏。
后来,我定居都市,绝少再回故乡。即便匆匆回家一趟,也不见七斤哥的踪影。只听村里人说,他农闲在外挖煤、打工,农忙在家种地、务农,日子过得艰苦,但很充实。我还听说他已结婚,生下一个儿子,用新秤一称,也是七斤!
最近,我又一次回到故乡,意外见到了七斤哥。他不再是《故乡》中的闰土形象。黝黑的脸庞与微驼的背脊写满了对命运不屈服的抗争与信心。他侃侃而谈,谈他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他说,他要倾其父爱,精心培养,让小七斤好好学习,永不失学。
往事与现实交替浮现我的脑海。我忽然觉得“七斤”只是生命的一个符号,而亲情与友情中所不能承载之轻,灵魂与命运中所不能承受之重,又怎能用老秤与新秤可称量得出来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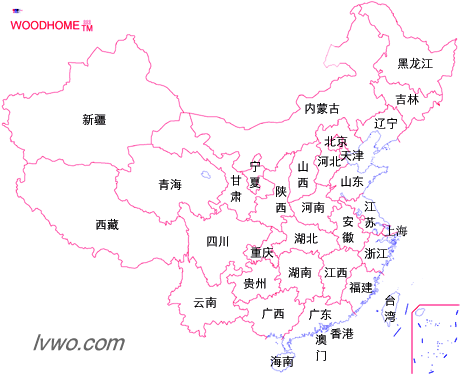


 十大顶级高端户外品牌...
十大顶级高端户外品牌... 全球户外品牌体系大起...
全球户外品牌体系大起... 全球顶级户外人体摄影...
全球顶级户外人体摄影... 女子裸体户外攀岩性感...
女子裸体户外攀岩性感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