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记忆的末端,有一条小溪,明朗的水折射出四季的色彩,活泼的鲜明的童话般的一溪活水,潺潺的跳跃在布谷鸟统治的山谷。
真的有那么一溪活水,在人迹罕至的山间,而山又坐落在喧嚣的小城的怀抱,慢慢的一点一点被房屋侵袭,但同时,它又是古时遗留下来的巍峨的林场,现在是自然保护区。于是每天坐在明朗的窗边,轻轻的就能听见它呼吸的声音,仿佛心爱的人亲切安详的睡在身边,我则轻轻的抚着她同样发丝明朗的额头,心灵平静的如同湖水一般。
那个纯朴的秀美的校园,就嵌在这崔巍的山峦,诡秘的林莽间,那里曾有过无数属于尘世以外的淳朴秀美的故事……
溪水咯咯的笑着到了那个校园,便转成了地下水,它是在操场的人工修整的成直角的山体上,安详明朗的跃下,清清的水帘如同平整的纯粹的水晶,不肯造就一丝的水花。
我曾经有过无数个月色明朗的傍晚,在那里让溪水丝丝的凉意淋在身上,冲走的仿佛不止有尘埃与汗汁,还有别的东西,拥抱溪水以后,便独自的溯源而上,疲倦的双腿踏进星星满天。
溪边所谓的路是陡峭的平滑的抛物线形的,它也慢慢的被两旁昏暗的齐人高的杂草侵蚀,冷冷的如同潜伏在草丛里巨蟒的脊背,夜的山风扫过,草抖动间扭曲出内心的荒芜。
我曾经有过一个要好的兄弟,他疯狂的爱上了一位如同溪水般同样秀气纯洁的女孩,那是一种能令人寝食不安的脆弱执著的感情,纯情到了痛苦的地步。
有一天,我与他逆流而上,高大的原始林木在地上留下一块块不规则的沉静的阴影,皮鞋跟清脆的声音回荡在静谧的山谷,回荡在布谷鸟与心情之间。
当身体留在地上的的影子靠近溪水,就能看见里面螃蟹敏捷的躲开的身影,将手指插入水里,指缝间丝丝滑过的是清爽,亲切,惬意,还有纯洁……
“我想在这里盖一间房子”。他给我的是那种呆呆的能迷到女孩的眼神。
“我也想”,我懒懒的望着有着树叶间漏下来的光柱子的洞天。
那时侯的心灵是荒芜的,其实心灵何尝不是一直荒芜着呢?我们这两个十七,八岁已该学会成人的大男孩,在山谷的溪边重复着自己的幼稚的秘密。
偷偷的,将小锄头装进书包,又买来铁钉和铁丝……
就这样,连续一个多月的傍晚,我和他都要准时的来到山谷的溪边……
曾经担心清脆的伐木声会被护林员发现,曾经用藤子荡秋千,曾经躺在花草间,看肚皮上的大螃蟹挥舞着大钳子漫无目的的游荡,曾经被有毒的毛虫烙出一道道条形红肿的痕迹,回到教室才发现。
那时侯在明朗的天空下,我们是用头顶着阴郁过日子的,我需要面对来自学业的父母的老师的重重压力,而自己的内心的前途则是一片迷惘,他不仅有这些,他还有着无法自拔的一腔痛苦的爱,然而自从开始幼稚的建那个小屋的时候,我的心里仿佛有了一种可以作为精神寄托的安详的充实感,头顶上重现一片明朗的天空,浮现于嘴角的终于是那种轻松的发自心底的笑了。
那小屋其实只能算得上一个蹩脚的窝棚,甚至连遮风挡雨都做不到,然而它在我们的心里却是那样的美丽,那样的珍视,我们别出心裁的把它装扮的很美,而且一直没有告诉别人这个秘密。
后来,那个女孩终于做了他的女朋友,我依旧每天傍晚漫步于布谷鸟山谷的溪边,只是不再走近那个小屋,我把属于我的那份小屋送给了她,希望他们能够快乐。奇怪的是,尽管不再靠近那个小屋,只要走进山谷,走进溪边,我就能感受到那种幸福的充实的轻松的快乐。
现在,在万里之外的长春,想起故乡,想起高中的日子,我终于明白了,我是将心灵一点一点的剁碎,撒在了那潺潺的溪水里,撒在了那幽幽的山谷间。
同为应试教育下枯燥的挺过来的莘莘学子,我是幸运的,我的少年时光不像他们一样挥霍于痛苦的机械的麻木的学业,因为我的心灵属于那片多彩的天光山谷和小溪,我生在了一个幸福的小城,小城包围着一个美丽的山谷,山谷里有一条明朗的奔腾的小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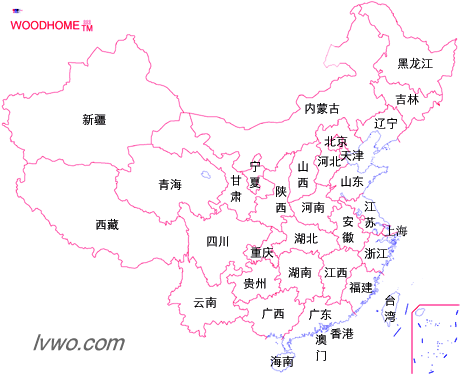


 十大顶级高端户外品牌...
十大顶级高端户外品牌... 全球户外品牌体系大起...
全球户外品牌体系大起... 全球顶级户外人体摄影...
全球顶级户外人体摄影... 女子裸体户外攀岩性感...
女子裸体户外攀岩性感...